男女主角分别是谢玉琰王晏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四合如意谢玉琰王晏全文+番茄》,由网络作家“谢玉琰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谢玉琰王晏是小说推荐《四合如意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,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,作者“谢玉琰”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,梗概:谢太后死在权势滔天的那一年。臭名昭著的她,不但没受到报应,反而穿到六十四年前。敌人尚未出生,她就赢在了起跑线,这就是做了祖宗的好处。……上辈子装作贤良淑德,却人人叫骂。这一生干脆不再遮掩。结果好像与她想的有些不同。打人,落得贤孝名。分家,族人自愿追随。杀人,也成了仗义之举。谢家娘子心善,人又好,大家都知晓。谢玉琰:惟愿天下安定,兴盛太平王晏:不信...
《四合如意谢玉琰王晏全文+番茄》精彩片段
“杨六哥为国效死,若这还不算忠义,什么才算得上?”
先开口的是一个瘸腿的男人,他也曾是个丘八,在战场上受了重伤,好在最终活了下来,得以返乡。
许多人就没他这么好运了。
有的甚至还被人割了头颅筑京观,那惨烈的情形,不曾亲眼见过的人,无法想象。
他们浴血奋战,马革裹尸,为的不是名声,可也容不得旁人质疑。
有人开了头,立即就有声音跟上。
“杨家三娘子教子有方,又舍身救人,自然也是大义。”
“我那侄儿就在静卫军,听说金明寨的那些将士,死守城池好几日,后来人都快死绝了,城门才被攻破。朝廷援军重新拿回金明寨,给他们收尸的时候,他们每人身上都拔出上斤的箭头。”
“怪不得他们大多数人骨殖无存,尸身残破的不成样子,哪里还能辨认出谁是谁。”
“永安坊出了这样的忠义之士,咱们也跟着脸上增光。”
“说的没错。”
“六哥儿在家中时,也一样听话,帮我遮过房顶,当时……唉……可怜这么小的年纪。”
陈举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声音,也觉得欣慰,本来刚刚他想要站出去先说话,却被王大人示意阻拦。
现在想想,他开口岂非本末倒置?这小娘子要的是坊中邻里对杨家母子的认同。
张氏环顾一周,看着那些为六哥儿正名的邻里,忙躬身行礼。在众人的声音中,不禁湿润了眼睛,当时六哥儿的死讯传来时,二房老太爷只顾着借这桩事光耀门楣,哪有半点的难过?
可是如今从身边众人脸上,她看到了许多同情、惋惜的情绪。
杨二老太太瞧着这阵仗,脸色难看,却不能表露出半点的不悦,被如此一搅和,以后族中谁也不能轻易为难张氏母子,否则张氏出门一哭诉,这些人说不得就会站在她那边。
早知会是这般结果,开始就该想个法子阻止。
现在一切都晚了。
杨老太太正在思量如何收场,人群向两边散开,紧接着一个年过五旬的男子走过来。
“禀贺巡检,下官方适,乃永安坊坊正。”
方适躬身,额头上的汗水也落下来。
这么冷的天,他却满头大汗,可想而知,这一路赶的有多急。这着实不能怪他,今日杨家失火,他这个里正免不了被责问,刚跑了一趟县衙,又被问起杨明山的案子,他马不停蹄又去了巡检衙门,在那里得知巡检大人不在衙门。
他从文吏那里看了公文,正准备请文吏喝酒,将此事来龙去脉再弄弄清楚,就听说巡检大人到了永安坊。
人赶到杨家门口,就瞧见了眼前这大阵仗。
方适都想要去庙里求张符了,他会不会无意中冲撞了哪位神仙?怎么今日发生的事,加起来比去年一年都多?
重要的是,永安坊惊动的还是刚到的贺巡检。
新官上任三把火,最难惹的就是才走马上任的大人们,更何况贺家乃武将世家,又有王氏这样的姻亲。
贺巡检脑门儿上就写了四个字:得罪不起。
幸好方适方才听到了众人谈论的事,当下也就接了过去:“方才我都听到了,杨三娘子大义救人,着实是一桩美谈,永安坊日后谁造谣生事、乱传不实之言,我定然将人拿办送去衙署。”
杨明经跟在方坊正身后,听到这话,心里漏了一拍,总觉得坊正这话,有意指向杨家。
知情不报的事还没解决,眼下又添了一桩。
而且……杨明经的眼皮跟着跳了跳,总觉得这还没完。
果然,一道声音再度响起。
谢玉琰道:“我既然被抬入了杨家,与杨六哥行了礼,就是结为了夫妇,日后必定好生奉养母亲,帮着母亲将九哥儿养大成人,全了这份情义。”
这话一出,周围免不了又是一阵议论。
贺檀道:“你可想好了?”
谢玉琰应声:“我被人掠卖来大名府,没有长辈在身边,也请巡检大人和诸位做个见证。”
贺檀点点头,看向张氏:“可有婚书?”
“有,”张氏道,“就在家中。”
“我去取。”杨钦说一声,就向院子里跑去,不一会儿功夫就将婚书送到贺檀面前,还递过了笔墨。
贺檀在婚书最后,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作保。
这婚事就算成了,没有人敢再说,这位“谢十娘”不是杨家的媳妇。
身边众人纷纷向张氏道喜。
杨明经却只听到头顶突然炸开了一记响雷。
杨二老太太更是半晌才反应过来,刚刚发生了什么事?那“谢十娘”要留在杨家?
还请贺檀做的保人,就这么定了?更吓人的是,那陈军将从方才起就一直盯着她,好像她只要敢上前阻拦,就会将她生吞活剥。
陈举心中欢喜,他早就说了,这桩事能成,他也算是第一次促成一桩婚事,日后还要时时提起。
思量到这里,陈举眼皮忽然一抽,心头也跟着发紧,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。怎么会有种不好的预感?
……
谢玉琰上前几步向贺檀行礼感谢,她也没忘记一直站在旁边的王鹤春。
别看王鹤春没说话,但她知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尽收他眼底。
她今日这般张扬何尝不是给他瞧的?
贺檀道:“日后遇到什么难事,可以来府衙寻我。”
谢玉琰点头。
便在这时,王鹤春递给杨钦几本书册:“明日来衙署,我带你去见城内的一位先生,他可教你读书。”
谢玉琰有些意外,她还以为贺檀要将杨钦叫去询问,再送出这些。
没想到,根本不必费那番周折,就被“他”猜透了。
不过仔细一想……大梁论读书谁又能及得上他?
这般聪明、懂得为人解忧。
谢玉琰下意识想要看赏。
心中这样想,却已经向王鹤春福了福身:“多谢大人。”
“我只是个书生,”王鹤春道,“离大人还差得远。”
是与家中那位老大人差得远吧?
谢玉琰自然不会与他争辩这些,眼下的王鹤春看着温和,谁知那双眼睛中暗藏多少汹涌。
不过,这样的人送到眼前,跟在后面的不知有多少利处,她得都接下。
王鹤春看着“谢十娘”再自然不过的目光,言语、举动自然而然,看不出有任何盘算的心思。
但那略带错愕接下他书册的杨钦,随即展开的笑容中分明带着几分钦佩,这钦佩自然不是给他的。
事情都办妥当,谢玉琰目送贺檀等人离开,转身要与张氏一同进门。
二房老太太目光阴沉,吩咐张氏道:“你与我过去说话。”
张氏自然应声,不过才走了几步,二房老太太就发现那谢氏居然也跟在了身后。
“你……”二老太太皱眉看向谢玉琰。
“我也有事要禀告老太太。”
二老太太皱眉刚要将谢玉琰打发了,却听到谢玉琰道:“方才老太太说,谢家是与老太爷议的亲,我想看看谢家送来的喜帖,上面写了陪送田产多少,嫁妆几何?”
杨钦三岁开始识字,父亲留下了许多书册,母亲捡着会的教他,等他稍大一些,就将不识得的字写下来,去问临坊的秀才。
其中有一本就是父亲手抄的大梁律,即便现在杨钦还不能都读懂,却知晓放火是什么罪责。
就算他这个年纪朝廷不抓他,族中也会惩戒,家里少不了花银钱。
当着贺巡检的面承认是自己做的,杨钦其实很害怕,尤其是看着贺巡检的神情变得更为严肃之后……
杨钦下意识地挺了挺脊背,他说了就不后悔,想到这里,他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穿着红嫁衣的谢玉琰,然后他立即就担心起来,不知道有没有被贺巡检发现。
正在杨钦思量之时,他感觉到头顶一暖,贺檀的手在上面轻轻地摸了摸。
小孩子的心事瞒不过大人,杨钦以为的“败露”,看在贺巡检眼中,杨钦是在确认那女子的安危。
什么样的情形,能让这么大的孩子不去求助家中大人,而是选择放火闹出动静。
“贺巡检,”杨明经再次试着开口,“我吩咐人去趟谢家,将他们唤来问清楚,毕竟这是谢家女眷,其中有何内情,我们也不知晓,您先去内院宽坐片刻,您看这样可好?”
杨明经只盼着贺巡检能答应,给他片刻功夫,让他来收拾乱局。
还没等到贺巡检应承,便又是一阵嘈杂的响动。
一个女子在尖利地叫喊。
“莫要找上我……冤有头债有主……不是我害死你……”
“我只是帮谢家遮掩……”
“我没有害你性命,不要找我索命。”
其中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哭声。
这声音杨明山再熟悉不过,是他的娘子邹氏。
杨家下人七手八脚将邹氏抬过来,邹氏还在不停地挣扎,尤其是看到一边的谢玉琰之后,邹氏满脸涨红,几乎又要晕厥过去。
场面一下子更加混乱起来。
杨明经却静默了,冷汗从他额头上淌下……
刚才邹氏的那些话再清楚不过,除非巡检有意偏袒,否则绝不会当做没发生。
杨明山就没有那般冷静,他到了邹氏身边,疾言厉色地道:“你在乱说些什么?”
邹氏见到自家郎君,眼睛登时一亮,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“阿郎,”邹氏恨不得缩进杨明山怀里,“她变成鬼,来害我们了,你快想想法子,是你与谢家议的亲,你去问问谢家,到底……”
“啪”地一声响动,邹氏眼前一黑,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,耳朵更是嗡鸣作响。
杨明山厉色道:“我看你是疯了。”
邹氏本就站不稳,被打之后,踉踉跄跄瘫坐在地上,惊恐和茫然中,她欲要再开口,杨明山又撸起了袖子。
“四弟。”杨明经开口提醒,杨明山才堪堪住手。
不用贺檀吩咐,陈举冷声道:“打够没有?我们可以再等等。”
案子没有审,但杨家坐实了知情不报,不管杨明山做些什么,在场这些人都能成为明证,还是他们亲手送到巡检面前的。
贺檀看向杨明经:“看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杨明经心中燃起一丝希望。
贺檀抬脚向外走去,杨明经立即要跟上,却被陈举挡住去路。
等贺巡检离开之后,陈举低声发令:“将人都带走,一个也别落下,再出什么人命案子,唯你们是问。”
这话是说给军巡卒的,却听得杨明经面色发白,这是在提点杨家。
两个婆子搀扶起谢玉琰,陈举目光扫到女子没有系紧的领口,忙转开脸看向杨明经。
“准备辆马车来。”
杨明经叫来几个婆子帮忙,将那女子和张氏、杨钦一并送上了车,正要松一口气,身后却传来陈举的声音。
“杨族长,”陈举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乜着他,“你侄儿是何月何日阵亡的?生辰是哪日?如今年几何?”
杨明经没有特意去记,又经过这样一通折腾,脑海中一片空白,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陈举抬头看了一眼杨氏门庭,发出声冷笑。
……
张氏和杨钦坐在马车中,怔愣地看着一旁的谢玉琰。
自从杨明生过世,她们母子第一次被族人这般礼遇。
小心翼翼这么多年,却比不上杨钦放的一把火。
“你没事吧?”张氏关切地道,“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坦?一会儿到了衙门,我去求那位陈军将,让他请个郎中来。”
“他们会请的,”谢玉琰道,“还会寻稳婆。”
稳婆是来给女眷验身的。
听到这话,张氏不禁有些担忧,她对谢玉琰一无所知。
“你从哪里来?身上可有难事?”张氏思量再三还是问出口,经过方才这一出,她对谢玉琰生出许多亲近之感。
谢玉琰是这些年来,第一个为他们母子出头的人。
闹出了大动静,狠狠地踩了杨明经和杨明山一脚。
谢玉琰摇头:“许是伤的太重,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醒来之后,谢玉琰第一件事,就是确定自己这具身体原主的身份,后来又听了张氏和邹氏的交谈,知晓自己并非谢十娘。
好在,她脸上没有刺字,身上没有鞭刑,头颈上没有戴过枷的痕迹。
谢玉琰说着自己的猜测,伸出手给张氏看:“手指间也没有劳作过,或是调琴留下的茧子,可见不曾进过教坊司。”
这些或许不全面,但这些大多能佐证她身家清白。
谢玉琰将手收回袖子:“我也希望衙署能查到我的身世,寻到我的家人。”
但谢玉琰觉得可能没那么容易。
她这身体的正主,没受过劳作之苦,指间却有握笔的茧子,谢家买具尸身而已,不用非得要个富贵人家的女眷。
她的来历,可能要费一番周折。
谢玉琰看向张氏:“你们呢?日后准备如何?”
张氏被问愣了,片刻后才道:“自然是……回家。”
谢玉琰看着茫然的张氏,换了一种问法:“杨家不能成为你们母子的依仗。”
张氏显然没想过这些:“我带着九郎离开杨家也不是不行,可杨氏毕竟是九郎的宗族,将来无论做什么,都绕不开宗族作保……”
她怕长辈为难,这才在族中忍气吞声。
张氏看到谢玉琰嘴角扬起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的笑容:“为何要离开?那些宅院、田地、族人不都是你们的?”
“我是让你另寻依仗。”
杨钦先反应过来:“要去哪里找?”
谢玉琰伸手向外指了指:“六郎早就给你们找好了。”
马车外是陈军将和一队老卒充作的军巡卒。
谢玉琰停顿片刻再次启唇:“不过,怜悯只是一时的,你想要他们庇护,就要对他们有用处。”
杨钦瞪大了眼睛,他知晓谢玉琰又在教他做坏事,可他很想听下去。
杨钦起身毕恭毕敬地拜在谢玉琰面前:“还请谢娘子教我,大恩大德没齿难忘。”
谢玉琰垂眼看着这小小的身影。
他唤过她“娘娘”、“圣人”,还是第一次唤她“谢娘子”,前世得他忠心追随,现在自然不可能看着他走老路。
……
贺檀带人回到巡检衙门,踏入二堂,就看到屋子里一个处置公文的影子。
“今日遇到一桩案子。”
那人影听到这话没有抬头,贺檀早就习惯了,并不在意。
“一个七岁的孩子,为了救人烧了自家祖宅。”
人影的笔仍旧没停。
贺檀道:“救下的是配冥婚的新娘子。”
“我问那孩子的时候,孩子没有隐瞒,承认了是他纵火,你怎么看?”
人影总算抬起头:“你被人利用了?”
“若是被人利用,他们说不得知晓你来大名府巡检的目的,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”
“娘,”杨明经低声道,“儿子方才那么说,只是权宜之计。”
杨明经不可能为了“谢十娘”与谢家为敌,两边孰轻孰重他根本不用去思量。
至于“谢十娘”那些话……
何氏低声道:“方才离得近,我瞧见谢氏手上,真的有握笔留的茧子。”
何氏父亲十九岁就中了秀才,可惜之后二十年,年年名落孙山。直到家中破落的不成样子,再也没有银钱供她父亲读书,家中人都劝何氏父亲放弃。何氏父亲犹不甘心,便将何氏许配给了杨明经,这才凑齐了赶考的银钱。
那时候的杨家二房可不是现在的风光,在族中没有田产,靠着三房讨生活。她因秀才女儿的名头,被三房老太太格外看重,早早就被安排在族中做事。
既然在这上面吃到了好处,何氏对读书人的那些事也就很关切,了解的也比寻常人多些。
谢十娘说话的时候,她刻意盯着谢十娘的右手去瞧。
中指上有一节皮肤粗糙,那是常年书写才会有的,身上也隐约露出几分书卷气。她能肯定谢氏读过书,这一点不会错。
只有高门大户,才有财力供一个女子这般写字。
以此推测谢氏不是出自寻常人家。
杨二老太太刚因杨明经的话松一口气,听何氏提及这些一颗心再次揪起来,眼睛都有些发红。
杨二老太太愤愤地道:“怎么就将她娶进门了?”
他们早就知道谢家会弄个尸身来顶替,却没料到谢家能在这上面出错,大名府每日都有女眷过世,怎么偏偏弄个没死的?
杨二老太太道:“那可怎么办?为着这些……就让她这般祸害杨家不成?”
杨二老太太想到一老话:请神容易送神难。
何氏道:“不过就算是这样,也只能说谢氏从前的日子过的不错。”
杨二老太太不明白。
何氏继续道:“大梁年年都有被砍头的官员,那些也都是读书人。也只有家道中落,家中女眷才能流落在外。”
“对,对,”杨二老太太从没觉得何氏这般贴心,“肯定是败落了!就她说的那番话,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家教出来的,家族气运注定不会长久。”
今天刚过门就骑在了她脖子上,为了大局让她退让一次也就罢了,绝不能每次都受这样的窝囊气。
杨二老太太恨不得早些收到消息,最好的结果就是,谢氏死爹、死妈,被灭了全族。
杨明经知晓二老太太的心思:“无论如何,得早点查清谢氏的身份,儿子想来想去,这桩事得交给谢家去办。”
“谢家由南到北运送米粮,方便打听消息,”杨明经道,“有些事不好查,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,拿着‘谢十娘’的画像和大致情形出去问,或许很快就能有结果。”
杨二老太太听得眼睛发亮:“谢家比我们更恼恨那‘谢十娘’,不怕他们不出力。到时一切查明白,看我怎么发落她。”
让“谢十娘”后悔今日这般顶撞她。
比起杨二老太太的欢喜,杨明经喜忧参半,“谢十娘”的身份交给谢家去查,但贺檀怎么办?贺巡检显然站在了“谢十娘”那边。
他有预感,贺檀不光是为了“谢十娘”这桩案子,而是借着这桩事,想要改变大名府的局面。
他听说朝廷要查商贾,到底如何查,他却不知道。
无论如何,杨家不能首当其冲。
难道真让四弟说中了,他得去请贺氏族中出面帮他向贺檀求情?
杨明经拿不准,贺家那些买卖,贺檀到底知不知晓?
杨明经心中一团乱,杨家是不能再出事了,可那谢十娘不是个省油的灯,让她本本分分,只怕不可能。
“娘、夫君,”何氏这时开口,“若你们怕那‘谢十娘’再生事端,不如找些事让她去做。”
杨二老太太看向何氏:“你有什么好主意?”
何氏嘴角微扬,露出一抹笑容。
……
三房母子的屋子,在杨氏祖宅的西北角。
小小的一间房,里面只有些破旧的家什,唯一让人能看过眼的,就是角落里的一张桌子,即便是这样,桌面都被补了好多次,可见她们的日子过的有多拮据。
杨钦刚进门就去折腾炭盆。
张氏道:“一日不在家,屋子里冷些,等端来炭盆就会好许多。”
前世杨钦与谢玉琰提及过,他母亲张氏死在一个很冷的冬日。
张氏找出两条最厚的被褥,铺在床上,让谢玉琰躺下去歇着:“你的伤还没好,身子又单薄,明日让钦哥儿去请个郎中,好好抓几付药回来补补。”
往常张氏是没这个银钱的,但杨六哥儿阵亡,朝廷送来了抚恤,有米粮和布帛,还给了六十多贯钱。
谢玉琰道:“能不能买到石炭?”
石炭不是窑中烧出的木炭,而是从地底下采出来的,前年开始有人贩卖,石炭比木炭扛烧,可价钱也是极贵。
“族中会卖些给我们,”张氏道,“但不好用。”
谢玉琰道:“在哪里?带我去看看。”
杨氏族中每年都会购置些石炭回来,好的留给二房自己用,差一些的卖给族人,到张氏这里的时候,花银钱只能买到碎末。
不买还不行,那是族中对他们母子的“照应”,这样的事不胜枚举。张氏每年在族中做事赚的银钱,也只能堪堪够他们母子度日。
张氏道:“族里确实比外面卖的便宜些。”
“那也得能用,”杨钦冷哼一声,“这么碎的石炭,丢在火里,烟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,闻久了还头晕,张秀才说,石炭有毒,用不得,会死人的。”
张秀才就是杨钦为自己寻的“野先生”,不用给束脩,只要哄得他欢喜了,就能教他几个字,还能将书上晦涩难懂的话,解释给他听,虽然大多时候,秀才解释完了,杨钦还是听不懂,但杨钦已经满足了,毕竟不要银钱。
谢玉琰看了那些堆积起来的石炭碎,又跟着张氏在这个小院子里转了一圈,这才又回到屋子。
杨钦已经将炭盆烧好,搬到了谢玉琰脚边,他眼睛中透出几分忧虑,恐怕谢玉琰看到他家中太过破烂,转身就走了。
“你们有什么打算?”谢玉琰道,“我知道朝廷给了些抚恤银钱,你们准备拿来做些什么?”
张氏摇摇头:“没……想过。”这些银钱,听起来不少,但请郎中吃药也极贵,用一用大约就差不多了。
谢玉琰道:“坊门要打开了。”
这个消息,张氏也听说了,早些年许多地方的坊墙都已经拆除,大名府是大梁的北方门户,因为战事一直没能行新政,现在北方战事少了,大名府可能就会与南边那些府城一样……
谢玉琰接着道:“坊墙拆除后,接下来就是解除宵禁。”
张氏懵懵懂懂:“你是说……出去做点小买卖?”她听说过,有些府城夜里还能遇到商贩卖东西。
“不光是卖东西,”谢玉琰道,“朝廷新政颁布,我们要赶在所有人之前应新政。将来提及大名府的新政,就要想到我们。”
张氏听明白了,可她却愣在那里。
提及新政,就要想到他们?这……怎么可能?他们哪里来的本事?
半晌,张氏才道:“我们……什么都没有,要怎么?”
“谁说什么都没有?”谢玉琰看向窗外,“我们不是还有杨家吗?”
谢玉琰话音刚落,外面传来叫喊声:“三娘子可在屋中吗?我家二娘子请您明日辰时去南院的小库房。”
张氏看向谢玉琰,谢玉琰点头:“看来我们想要的东西,得从那里找了。”
巡检衙门大牢里。
杨明山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惨呼声,手不禁下意识地颤抖,只要狱卒经过,他就呼吸急促,生怕他们的脚停在他面前。
昨日他还盘算着衙署什么时候能放他归家,光凭一个“谢氏”的案子,就算是巡检衙门,也留不了他多久。
毕竟从掠卖人手中买尸身的是谢家,再说那女人活了下来,总不能在他们头上记一条人命,最坏的结果,就是被打几板子。
可哪里料到事情会急转直下,他不但没能走出大牢,反而有更多人被送过来。
当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时,杨明山心里满是震惊,尤其是看到父亲被人拖着丢入牢房,他整个人都被恐惧所笼罩。
到这里,还没完。
他还看到了杜太爷和永安坊的几个老者。
然后,杨明山从这些人谩骂杨家的话语中,猜到了真相,他们私运番货的事被朝廷查到了。
接下来,这一晚格外的漫长。
杨明山每一刻都在极度惊惧中度过,尤其是听到那一声声惨叫,狱卒手中的鞭子好像抽在了他身上。
牢房中开始有人告饶,有人哭泣。
没等衙署提审,很多人就说出了实情,杨明山也屡屡听到自己的名字。
“都是杨明山,是他将青白盐卖给我的。”
“庄子是二老太爷买给四老爷的。”
“总会让我们将货物送去庄子上,有时候往西北送,就送去个货栈。”
“那货栈在哪里我知晓。”
“见过高高大大的商贾,听着说话怪怪的,说不定就是与四老爷勾结的番人。”
“我说的都是实话,我们也是听四老爷的吩咐做事。”
杨明山一颗心跌入谷底。
这么多人将他供述出来,可是衙署偏偏没有来提审他,就像是在等死一般,格外的煎熬。
终于熬到了天亮,大牢里的审讯却始终没有停下来。
迷迷糊糊中,杨明山听到父亲的声音。
“那庄子是我买给他的,但我不知他都做了些什么,”杨二老太爷咳嗽着道,“我还以为他只是从族中赚点好处,让我见见那畜生,亲口讯问他,让他招认清楚。”
北城外的庄子,是杨明山亲手打理的,谁都能脱身唯有他不行,更何况……最近确实都是他带着商队往西北去。
“不是我爹,我爹没做过。”
一个突兀的声音夹在其中。
杨明山眼睛一亮,那是他的长子杨骥。
“你们都在乱说些什么?”杨骥继续为杨明山辩解,“不要什么污水都泼在我爹身上,那庄子我也去过,根本没有私藏什么货物。”
“你也逃不了,”杜太爷道,“你父亲最看重你,这些事定然与你说过。我与你父亲买卖的账目都交给了衙署,你们将青白盐丢给我,出事了想要拿杜家顶缸?做梦。”杜家这次是完了,他也不能让杨家逃脱,尤其是怂恿他走私货的杨明山。
杨明山整个人瘫了下去。有杜太爷在,他不得逃脱,却不能将骥哥儿再卷进来,如果他被判了徒刑,还需要有人在外帮他打点,也能让他早些归家。
杨明山拿定了主意,等到他被提审时,就算严刑拷打,他也决计不会牵扯骥哥儿,却在这时,他听到一个声音传来。
“谁也逃不了。”
杨明山下意识地顺着声音看去。
牢门刚好被打开,几个人影就立在不远处。
说话的是个女子,她看着眼前的人。
“不是徒刑,更不是流放,你活不成了……”
杨明山整颗心被攥住,他怔怔地看着那女子,隶卒手中提着的灯亮了几分,女子的面容也清晰了许多。
那是“谢氏”。
“谢氏”面前的人,因为这话也跟着一抖,紧接着谢氏似是又说了些什么,这句话杨明山听不清楚,但他却看到那人刚刚挺起的脊背又弯了下去。
明知道“谢氏”是在与那人说话,可杨明山却觉得,“谢氏”就是故意让他听到。因为他和杨骥也是那个“活不成”的人。
杨明山怔愣间,狱卒押着那人往前走,路过杨明山面前时,那人转头去看杨明山,杨明山眼睛又是一缩,那张脸孔他很熟悉,是谢崇峻身边的吴管事。
谢家也被牵扯了进来。
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吴管事,眼下也是落魄又慌张,眼睛中满是复杂的情绪,不知在想些什么,仿佛好半晌才认出了杨明山。
吴管事要说些什么,却被狱卒推了一把,立即又向前走去。
……
吴管事是跟着谢崇峻前来巡检衙门认罪的。
从谢家决定与杨家结亲,一切就是吴管事在操持,所以……谢家让他担下所有的罪名,吴管事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
大老爷答应这桩事后,就将卖身契还给他,从此之后他们一家不再是私奴。
他们会恢复良人的身份,单独在大名府落户,这对他来说,是极大的诱惑。
这么一看,这也是件好事,就算衙署判重了,说他私通掠卖人,他也罪不至死,反而能让一家人脱贱籍,所以他拿定主意,都照大老爷的吩咐去做。
可是没想到,会在衙署遇到那“谢氏”。
吴管事是见过“谢氏”尸身的,听说“谢氏”死而复生,他就觉得惊奇,如今见到活生生的人……
不知为什么,他反而更加恐惧起来。
“谢氏”看向他时,目光中满是寒意……让他想起一些不好的事。
他从牙婆手中买到尸身后,曾仔细探看过,还伸手试过“谢氏”的鼻息,从鼻尖传来的冰凉感,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些细节,一股脑地涌出来,让他觉得眼前的“谢氏”,比起人来更像鬼。
谢氏开口说的那句话,更加可怖。
“不是徒刑,更不是流放,你活不成了……”
她好似什么都知道。
“若是谢氏允诺你的事,没有做到,反而要向你们下手,”谢玉琰道,“可以来寻我,我会帮你们。”
“谢氏”说完话,吴管事忽然感觉到一阵冷风从他领口灌入,灯光明灭不定,“谢氏”的身影好似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吴管事仿佛丢了魂魄,迷迷糊糊地往前走,冷不防看到了大牢里的杨明山,紧接着他从杨明山的目光中也看到了相同的恐惧。
惊恐的时候,遇到一样惊恐的人,只会觉得更加可怕。
吴管事脚下踉跄,他感觉到又有一魂一魄脱离了他的身体。
……
站在大牢外的谢崇峻似是听到一些动静,可惜离得太远,着实听不清楚。
应该是有犯人在喊冤。
谢崇峻深吸一口气,就要抬步离开,面前的牢门却在这时候又打开,然后一截藕色的裙裾出现在他面前。
郑氏带着谢玉琰找到牙婆,几人就在安义坊内寻租赁的房屋。
冬日里,牙行的买卖不好,所以即便知晓谢玉琰赁的屋子小,赚不到多少佣钱,牙婆也卖力的忙乎着。
“娘子,你看看这间屋子如何?”牙婆脸上满是笑容,热络地将房门打开,“虽说比之前那间小了些,价钱却便宜。”
牙婆说着顿了顿,然后伸出两根手指:“一年只需两贯钱。”
一间小屋子,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,角落里都是落叶和泥土,显然许久没人住了。
谢玉琰抬起头:“屋顶可结实?”
“娘子放心,入秋之后,我亲眼看着他们修葺的,便是有多大的雪也压不塌,用到明年定是没问题,”牙婆接着道,“就是小了些,不然这里靠着西市,早就赁给那些货郎了。”
来往的货郎,总要在屋子里存放些物什,还要有浑家守门,这么个地方搬进些家什就没处下脚了。
“还是贵了些,”郑氏不禁道,“总要再少个几百文。”
村中盖房子,一间不过就是几贯钱,虽说只是个茅草屋,但……这房子破旧的样子,也好不到哪去。郑氏也是不知晓谢娘子赁这么个屋子做什么用处,这一路过来,她就是瞧着谢娘子似是不太会压价钱,这才开口帮忙。
“最近这附近街巷的屋子买卖、租赁都贵了些,”牙婆道,“也就这安义坊不比周围几个坊兴盛,这里住着的人,不少都在瓦子、脚店做活计,寻常人不愿与他们相邻,若非娘子看好了地方,我定会为娘子寻旁处。”
“要说少,顶多只能再少个一百文。”
谢玉琰点点头:“那就是这里吧!”
牙婆立即眉开眼笑:“老婆子这就跟娘子去做文书。”
谢娘子做了决定,郑氏也就不再有别的言语。谢玉琰给了两百文做定钱,约好明日让人再将剩下的送给屋子的主家。
将牙婆打发走了,看着眼前简陋的屋子,谢玉琰看向郑氏:“郑娘子方才说想要卖藕炭?”
郑氏点点头。
谢玉琰道:“我赁这屋子也是因为藕炭。”
郑氏不禁一怔:“娘子是要在这里卖藕炭?”
谢玉琰摇头道:“我要开间水铺,在这里卖热水,我看郑娘子也是伶俐人,愿不愿意在这里帮忙?只是烧水做些杂务,每日铜钱六十文,卖出藕炭另算银钱。”
郑氏哪成想还能再寻到别的活计?
就像天上掉了银钱落在她身上,郑氏半晌都回不过神,不过想想自己的情形……
郑氏面色又是一暗,她咬咬牙,终于下定决心,缓缓将自己的左手伸出来:“好让娘子知晓,我有一只手不堪用……”
她一直羞于将这露于人前,恐遭嫌弃,现在却如何也不能遮掩了,恐怕谢玉琰会追问,郑氏忙道:“村中曾进山匪,我这手就是那时落下的伤。”
就是因为这个,她也寻不到什么活计来做。
这次……也会如此。
郑氏正想着,就听得谢玉琰道:“只是烧水,不是精细的活计,郑娘子也应付不来吗?”
“能,能的,”郑氏惊喜地抬头,“我能做。”
谢玉琰道:“那就是了,郑娘子做好了这些,六十文钱不会少。”
郑氏脸上不禁浮起笑容,不过欣喜过后,又夹杂了一抹忐忑,郑氏想了想再次问道:“娘子是要用藕炭烧热水来卖?”
怪不得会选安义坊这样的地方,许多人家冬日里为了省柴禾,就在水铺买热水。尤其是在瓦子做行当的那些人,冬日难寻到什么活计,尽可能的不烧灶,早晨能就着热水吃些冷饭,对他们来说就是极好的了。
谢玉琰道:“街市上秸秆要二十九文一束,便是柴也要七十文一担,我们的藕炭虽然没有秸秆便宜,却比用柴划算,而且与木炭一样,烧起来没有太多烟尘。我们用藕炭烧水,即便不能赚太多银钱,却能因此让大家看到藕炭的好处,你说是不是?”
谢玉琰这样一说,郑氏心里更加通透。坊间都说石炭有毒,开了水铺,有毒没毒大家一看便知,如此就不用费尽口舌去劝说了。
怪不得谢娘子说,卖出藕炭另算银钱,大家看到藕炭的好处,一斤藕炭不过三文钱,入冬之后木炭一斤却要十一、二文,哪有不买藕炭的道理?
谢玉琰道:“我还准备在附近几个坊,也寻两间差不多的铺子,若是郑娘子愿意,就帮我去办这些事,我也按每日给你结工钱。”
“不用,不用,”郑氏忙摆手,“左右我在家中无事可做,谢娘子能信得过,我便去帮谢娘子去打听,原本也是我们得了好处。”
郑氏说着拽了拽自己破旧的衣裙。
谢玉琰摇头:“我让郑娘子卖藕炭,是因为你们在大名府久了,认识的乡邻更多,并非你们得了我的好处。你们赚的本就是辛苦钱,用不着谢谁。”
“但我也有规矩,藕炭只能按我定的价钱卖,每卖出三斤藕炭,我给你们一文钱,不得卖高价,否则日后就不用跟着我做买卖了。”
郑氏连忙点头:“不敢,都按娘子说的做。”
谢玉琰接着道:“即便卖不出藕炭,我也会分给你们每家三块,不算银钱。”
郑氏立即摆手:“这可使不得……”
谢玉琰打断郑氏的话:“我给你们藕炭,与开水铺子是一样的,有人用,才能卖的出去。”
郑氏抿了抿嘴唇:“谢娘子怎会如此信我?”
若非受尽欺压,不会得了一点点好处就露出惴惴难安的神情。郑氏的品性如何,谢玉琰一眼就能看透。
谢玉琰道:“既然都在童先生那里进学,陈平和我家九郎就有同窗之谊,我让九郎送藕炭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“再说,刚刚我与郑娘子也才见面,郑娘子不也在尽心帮忙?”
郑氏捏着手,半晌才说出一句:“谢娘子和童先生一样,都是……极好的人。谢娘子信我,我定会将谢娘子交待的事都做好。”
重新将门锁好,谢玉琰将钥匙交给郑氏,嘱咐郑氏一些活计,这才转身离开。郑氏站在原地,一直等着谢玉琰的身影再也瞧不见了,才低下头看着手中的钱袋。她从家中出来的时候,想着的只是能卖藕炭,哪知能有这结果,许是……老天爷真的开了眼,愿意伸手救他们了?
等郑氏也走了,躲在角落里的人影才闪身出来,他看了看周围,没有发现什么异样,这才转身跑了出去。
那人一口气跑出两条街,才进了一处茶楼,奔到楼上的隔间推门而入。
“七爷。”那人看向坐在椅子上的谢七爷。
谢七爷正怀抱着一个美妓调笑,见到自家小厮,挥手将怀中女子赶走,这才问小厮:“探听了些什么消息?”
那小厮开口道:“谢家娘子赁了一间屋子,好似要做水铺买卖。”
谢七爷没有说话,继续听着,谁知那小厮没有了后话。
“没了?”
小厮点头:“没了,就……就这些。”
在杨家闹出那么大的动静,最后就是要开一间水铺?谢七爷本来发着光亮的眼睛,突然就暗淡了几分。
他对那位谢娘子很感兴趣,如果她仅仅就是这点本事,他可是会失望的。
谢七爷正在思量,外面又传来脚步声,紧接着谢家管事进来道:“七爷,老太爷唤您回去呢。”
谢七爷微微抬了抬眉毛,怎么?那老家伙终于坐不住,要亲自过问杨家“谢十娘”的事了?
杨家二老太爷都被抓了,老家伙也是该担心,这把火到底能不能烧着谢家了。
王鹤春会顺着贺檀的话想起这些,并非觉得谢娘子有失礼之处,相反的,他一直没感觉到奇怪,好似就该如此。
方才在杨家,所有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中,之所以现在还看不出她有多少本事,是因为杨家太小,不够她去施展。
他笃定她出身世家,但大梁的世家早就没落,没了往日的风骨,只是明里暗里为自家利益无尽的争斗,即便靠着声望做些事,也都是表面的功夫,男子都很难有出挑的人物,更没听说哪家有这般厉害手段的女眷。
王鹤春将脑海中那些念头赶出去,这也是他不喜欢京城的原因,他思量着,起身走到兵器架前,伸手去摸上面的一杆铁枪,脑海中其余的念头都被屏蔽在外,剩下的是尸身血海,惨烈的战事。
“大公子,可使不得。”
惊诧的喊声传来,王鹤春才回过神,他转过头去,看到自家家奴跪在地上,满脸惶恐。
周管事日夜兼程来大名府送信,没想到一眼就看到自家大公子握着那杆铁枪,登时吓得魂飞魄散。
他以为那件事后,公子就彻底断了去军中的念头,难不成……
贺檀一旁道:“鹤春就是随便看看,你这般惊诧做什么?”
周管事深吸一口气:“是老奴没了规矩,向公子请罪。”那桩事知晓的人不多,就算是王家,也差点面临灭顶之灾,他这是落下了心病,瞧见公子动这些刀枪就害怕。
王鹤春重新坐回椅子上,吩咐周管事起身:“家中可是有什么事?为何突然赶来大名府?”
周管事道:“眼见就要过年了,夫人惦念着公子,让我们借着四处送年礼,也给公子带来些东西。”
听到周管事提及母亲,王鹤春的目光柔和几分:“母亲身子可还好?”
周管事点头:“公子才离京的时候,夫人染了风寒,不过很快就康健了,倒是老爷公务繁忙,愈发消瘦了些。”
王鹤春知晓父亲政务繁重,往常在家中,他都会帮着分担,现在少了臂助,免不了操劳。
王鹤春道:“我写封家书,你带回去给母亲。”
周管事应声。
贺檀笑着道:“有我在鹤春身边,让姨母安心,等大名府这边安稳了,我就将鹤春放回京城。”
周管事连连点头,站在一旁等着王鹤春写好了信笺,这才拿着准备退下。
王鹤春将他叫住:“你在京中可听到哪个达官显贵家的女眷出了事?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,尚待字闺中。”
公子甚少提及女眷,周管事精神就是一振:“大爷说出事……指的是……”
王鹤春道:“或是突然生了病症,或是亡故,从前常常帮着掌家,突然就没了消息。”
世家名门的女眷,就算丢失,也会设法遮掩,免得坏了族中名声,所以他才会这样发问。他也让人去打听消息,只不过时间太短,还不曾有回音。
周管事仔细想了想然后摇头:“并未听说。”
“公子离京后,最大的事,就是淮郡王与谢老相爷的孙女订了亲,当今圣人特意赏赐谢氏两箱东西做贺仪,达官显贵也都登门恭贺。”
谢氏是大梁名门望族,谢相爷曾深受皇上器重,谢氏子孙多人在朝,如今又与皇族攀亲,自然风光无限。
眼下大名府也有谢氏,不知两个“谢”是否有牵连。
“淮郡王还亲自前来请公子去宴席,被老爷应付了过去。”
说完这些,周管事抬起头看向自家公子,欲言又止。自家公子总有种威势让人心生惧意,这一点不输自家老爷。
王鹤春淡淡地道:“还有什么事?”
周管事抿了抿嘴唇:“崔家送来消息,太夫人病重,恐怕就是这一两年的事了,那边说,若公子得了空,就往崔家走一趟。”
自从祖母与祖父和离回到崔家后,王鹤春就没再见过她。这几年祖母让人送来几次消息,让他前去相见,他却都没有应承。
王鹤春点头:“我知晓了。”
公子这样回应,在周管事猜测之中,崔家想要缓和两家的关系,公子这一关只怕过不去。
以公子的性子,别说一个崔家,就算是老爷也无可奈何。
周管事退下之后,屋子里只剩下王鹤春和贺檀。
贺檀踌躇片刻,没有开口提崔家,王家的家事鹤春自有主意,用不着他来劝说。
“如果大名府这个谢家与开封谢氏有关系,只怕没那么容易对付,”贺檀道,“要不要让人知会谢小娘子一声?”
谢氏自然不可能动他,但谢小娘子却不同,即便掌控了杨家中馈,说到底杨氏也不过一个小小商贾,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被算计。
“不用,”王鹤春脑海中浮现起,谢玉琰那双清澈、淡然的眼睛,“她自有思量。”
贺檀道:“不知谢小娘子接下来要如何做?”
这么快就帮他们破局,贺檀还好奇那小娘子又会用出什么手段。
王鹤春知晓她该从哪里下手,但到底如何做,他现在还无从猜想,但他预感,谢玉琰会比他推测的做的更好。
贺檀站起身:“咱们去大牢看看吧!”
这时候杨家人应该吓得差不多了。
……
永安坊,杨家。
何氏面色难看地靠在软塌上,她就是在这里,将管家的权柄暂时交给谢氏的,可她没想到仅仅半日的功夫,谢氏就将杨家变成这般模样。
族中牵连进去那么多人,谢氏还要从头彻查账目。闹得族中人人自危,方才就有不少人挤在她屋中,盼着她能为她们做主。
可现在她都不知晓,是否还能收回中馈大权?
何氏早就后悔了,她不该那么轻易信了谢氏的话,现在杨明山肯定要倒了,但只怕他们也没什么好结果。
“娘子,”管事妈妈上前道,“于妈妈回来了。”
何氏精神一振,她将于妈妈派到谢氏身边,就是要清楚知晓谢氏动向,虽然于妈妈一直不曾送任何消息回来,但可能是被绊住无法脱身。
主仆这么多年的情分在,何氏还是对于妈妈抱着一线希望。
“二娘子。”于妈妈进门行礼。
从前于妈妈就直接唤她“娘子”,“二娘子”多少显得生分。何氏却也顾不得这些,忙着问:“谢氏那边怎么样?她是如何思量的?到底要做什么?”
于妈妈没有开口。
何氏皱起眉头:“她是不是吩咐你与那些郎妇去做事?”
这次于妈妈点了点头。
何氏就要追问,于妈妈道:“但奴婢不能告知二娘子。”
何氏面容一僵,整个人怔在那里,旁边的徐妈妈见状插嘴:“二娘子这些年对咱们不薄,你可别犯了糊涂。”
于妈妈抬起眼睛,脸上虽有一丝怯意,目光却很是坚定:“这些年奴婢尽心尽力为二娘子办事,不曾有半点疏忽。”
“二娘子让奴婢去大娘子身边,奴婢也想着做好差事回来复命,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……奴婢现在……回不来了。”
这是背叛恩主。
这才几个时辰啊!
何氏心中燃起怒火:“我就算养一条狗,也不会这般。”边说边将手中的暖炉丢掷出去。
暖炉砸在于妈妈身上,还热着的炭火洒出来,烧着了于妈妈的裙角,于妈妈没有急着扑火,任由身上冒起屡屡青烟。
片刻之后,于妈妈才又开口:“二老太爷进了大牢,奴婢总要担些干系,二娘子念在孝义当先,不可能再用奴婢,甚至还会对奴婢加以惩治。更何况奴婢也没及时传回任何消息,日后二娘子只会愈生猜疑。无论怎么想,奴婢回来都是条死路。”
何氏气急:“这都是谢氏的手段。”
于妈妈点头:“是,既然斗不过就只能追随。奴婢这些做下人的,没法选出身,但跟个厉害的主子,也能活得轻松些。”
何氏胸口一疼,就要再开口训斥。
于妈妈接着道:“用不了多久,二娘子也得听谢大娘子之命行事,奴婢怂恿二娘子与谢大娘子为难,会死得更惨。二娘子看在奴婢追随这么久的份儿上,赏奴婢一条活路。”
于妈妈说完躬身叩首。
何氏哪里听得进许多话,她就想打死眼前这个没良心的东西,心里想着,手抄起了桌边的瓷盘,就要向于妈妈头上砸去。
就在这时,门口却传来下人的禀告。
“三房……那边的谢大娘子让人来寻于妈妈,”下人道,“让于妈妈立即过去侍奉。”
何氏的手僵在半空中,她抿紧了嘴唇,几次想将瓷盘脱手,无形中却似有个力道,将她的手臂牢牢握住。
地上的于妈妈爬起来,彻底抖掉了身上的炭火:“奴婢告退。”
踏出了房门,于妈妈才听到背后传来碎瓷的响动,她深吸一口气,看来她没有选错。从今往后,她不必再有别的心思,紧紧跟随大娘子就好……
因为,没有什么后果,比背离大娘子更加可怕。
……
大名府城外,陈窑村。
陈平靠在一旁睡着了,今晚他感觉到格外的暖和,都是因为杨钦给他分的这些藕炭,他的母亲郑氏却没有睡。
郑氏看着藕炭上发出的火光,目光涣散,不知在思量些什么。
不一会儿功夫,陈家大门被人敲响,郑氏起身去开门,只见是同村的两个妇人。
“你听说了吗?”
三个人进了门,其中一个妇人就迫不及待地道:“永安坊那边出事了,巡检衙门抓了好多人,听说……是因为私运番货……”
另一个显然也被这消息振奋:“我们要不要去巡检衙门试试……我们……”
郑氏低下头将左臂从袖子里伸出,手臂一端连着的左手无力地耷拉着,就像一朵早就枯萎的花,轻轻一碰就会碎裂。
郑氏神情显得有些木然,她缓缓开口道:“我的手怎么丢的,你们都忘记了?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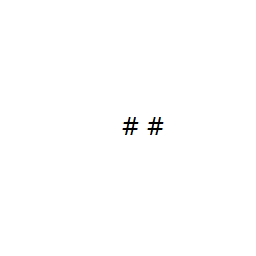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